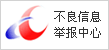|
編者按:在編輯“文化周刊”中,我們經(jīng)常收到一些讀者和作者就本刊文章提出不同意見,展開商榷和爭鳴。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,這正是學(xué)術(shù)繁榮的生動體現(xiàn),也是為我們所期待和歡迎的,為此,本期“文化周刊”特刊發(fā)就上月本刊發(fā)表的《語言病相與文化自信》和《藝術(shù)人生不是落淚人生》兩篇文章提出異議的來稿,進(jìn)行學(xué)術(shù)商榷和爭鳴。 我們期待更多的讀者和作者支持和關(guān)注本報。 貴報2003年12月29日《文化周刊》“文化回聲”發(fā)表林可先生的《語言病相與文化自信》一文中指出:“在商業(yè)背景中滋生的語言現(xiàn)象不能由商業(yè)來承擔(dān),就像網(wǎng)絡(luò)上語言暴力不能由引領(lǐng)科技潮流的網(wǎng)絡(luò)承擔(dān)一樣。真正需要反省的,是我們所處的文化。”在這里先要了解一下什么叫文化,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,文化并不等同于知識,文化是人類在歷史發(fā)展過程中所創(chuàng)造的物質(zhì)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,文化是人類創(chuàng)造的物質(zhì)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歷史積淀及其在當(dāng)代的新發(fā)展。由此看出林可先生的精辟論證無可辯駁,但是我覺得領(lǐng)導(dǎo)文化主流的還是經(jīng)濟(jì),在我們物質(zhì)建設(shè)取得許多成效而歡欣鼓舞的同時,我們也發(fā)現(xiàn)一些貌似新文化,實際上是把一些低俗的東西改頭換面重新包裝后又粉墨登場的現(xiàn)象。究其原因,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商業(yè)沖擊下對文化理念的不解、淺解、誤解。由此我想到一個說法:商場也打著人文的旗號,也不斷地裝潢門面,也不斷地美化環(huán)境,但是,商場永遠(yuǎn)也改不了“消費者購物,商家贏利”的宗旨。 林先生對我的文章《在商業(yè)背景中滋生的語言和文化問題》一文(“文化回聲”2003年12月22日)頗多感慨,也有一種誤解,“如果看到月亮就首先想到‘皎潔’,或者看到到‘皎潔’就認(rèn)為它只能用來形容月亮,對于一位作家來說,這是想像力的匱乏。”難道那些美女作家、美男作家的想象力也匱乏?可其作品里充斥的種種病態(tài)語難道不是語言運用中的盲點嗎?“痞子文學(xué)”之后,“武俠文學(xué)”已經(jīng)蔚成大觀,還有什么“想象力匱乏”可言?到底還是語言與文化功底問題。 不過林可先生提到的文化自信這個觀點我非常贊同。中國幾千年形成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是一份寶貴財富,中華民族歷來就是以其博大精深的傳統(tǒng)文化來融合周圍民族的,在商業(yè)文化建設(shè)中,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生生不息剛健文明的創(chuàng)造精神等能幫助現(xiàn)代商家形成參與競賽所必須的獨特的文化氣質(zhì)和無畏氣概,有助于塑造勵精圖治的,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現(xiàn)代商業(yè)精神。眾所周知,日本和亞洲“四小龍”的商業(yè)文化就充分吸收、融合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。但林可先生針對種種語言病象說:“語言墮落的背后,是一種文化的頹敗,……這種文化,在面對自身的不良習(xí)俗和外來文化時,必然面臨一種力不從心的尷尬選擇,表現(xiàn)出極度的不自信。”并列舉了一些顯示了我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的不自信的現(xiàn)象。林先生的苦心,無非想證明一下商業(yè)浪潮帶給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,并多少包含著以下意思:“國人的知識結(jié)構(gòu)失衡,生產(chǎn)知識畸形增長,生存知識相對萎縮,我們正面臨一場文化自信與人文精神頹廢的劇烈沖突的危機。” 我認(rèn)為這與人文關(guān)懷嚴(yán)重缺失存在必然聯(lián)系。不少商業(yè)文化騙子打著人文精神的名,行著害文取利的實,把人文精神歪曲誤解。這里所說的“人文精神”一是基于語言文字本身內(nèi)容的,即語言文字的動人韻律、美妙的筆形、樸素或華麗的辭采、積淀于語言文字本身的深刻的文化內(nèi)涵等等;二是基于語言文字所負(fù)載的內(nèi)容的,如對祖國的忠貞、對民族的熱愛、對山川的贊美、對他人的熱情、對全人類的博愛、對社會的責(zé)任、對集體的熱忱、對母親的報答、對愛情的真誠等等。這才是真正的人文!可是當(dāng)今商業(yè)引導(dǎo)下的語言思想貧乏、蒼白,情感貧弱、無力,我們一方面明知國人的人文精神的缺失,一方面又把語言文字的宣傳與精神游離開來,如同把一個人的血肉分開。這樣,我們的文化怎么還有自信可言? 應(yīng)該擔(dān)憂的是當(dāng)國外許多時尚文化正大踏步向前的時候,我們的文化虛假自信同時存在。一袋極普通的食品廣告卻提醒我們:它同時意味著人的興旺、家庭旺、身體旺、事業(yè)旺、愛情旺……總之無所不旺。在商業(yè)利益的趨使下,所有的文化資源都有可能被這一文化形態(tài)納入市場,這一策略甚至使一些文化經(jīng)典也在劫難逃了。在韶山毛家灣,一家飯店高掛著當(dāng)年毛澤東當(dāng)年回鄉(xiāng)的照片,不過它想讓人們想起的已經(jīng)不是“紅旗高卷農(nóng)奴戟,黑手高懸霸主鞭”,而是主席生前愛吃的紅燒肉。在北京,一家家以“老知青”、“北大荒”為名的飯鋪紛紛開業(yè),張羅一些窩窩頭、高粱米飯,軍用書包……以供人們“懷舊”,然后順理成章地從“知青兄弟”們的口袋里掏錢。于是在“太陽最紅,毛主席最親”的優(yōu)美旋律中,我們看到了“紅太陽牛肉干”的巨幅廣告。黑五類、紅五類這類的商品及其廣告也應(yīng)運而生。 當(dāng)然,這些“文化經(jīng)典”只不過是給各種身份的人當(dāng)作一種文化消費品罷了。但是這些“新偽文化”在無所顧忌地消解著自身之外的所有意識形態(tài),使人們對經(jīng)典和傳統(tǒng)已不再懷有敬畏、不再懷有珍惜和“絕望”之感,一個“超越”的動詞,就足以戰(zhàn)勝所有的經(jīng)典和圣言。因此,這種消解是可怕的,它使經(jīng)典不再具有經(jīng)典的意義,在世俗化的過程中,所有的權(quán)威都將失去光彩。商業(yè)語言病態(tài)也許喚起了人們的消費欲望,并許諾在消費中可獲得一種集體幻想的滿足。于是便有了眾多“帝王”、“富豪”為名的物品,公寓則“羅馬”命名,一家小小的酒吧卻冠以“夜巴黎”的輝煌。人們在這里幻想,想象著自己是帝王、是富豪,想象著自己坐擁羅馬,或者正漫步于巴黎街頭,吸引著他們的,當(dāng)然已經(jīng)不是巴士底獄和公社社員墻,而是香水和時裝。上文所列現(xiàn)象,是在“精神家園建設(shè)”實施過程中,發(fā)現(xiàn)的一些與新文化理念貌合神離的做法,姑妄稱之為“偽新文化”。這些都是文化消費的虛假自信,并給我們真正的文化自信帶來致命打擊。 近幾年來,各國之間貿(mào)易爭端迭出,產(chǎn)生這些爭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國文化的差異和沖突,經(jīng)濟(jì)與文化是一對相伴相隨的孿生兄弟。各國、各民族的文化傳統(tǒng)的不同,對經(jīng)濟(jì)活動、經(jīng)濟(jì)行為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。曾經(jīng)日本被認(rèn)為是盲目崇拜西方,被西方文化灌輸而幾乎忘記了根本的國家。可是現(xiàn)在突然之間日本卻對世界文化產(chǎn)生一定影響。日本的動畫、設(shè)計、游戲、音樂、建筑已經(jīng)在世界上占據(jù)了重要的地位,有些甚至已經(jīng)是很多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了。日本人也談他們的文化自信。 每個民族都有其特定的禮俗,它構(gòu)成了一個民族的行為特征。由于文化背景、物質(zhì)背景以及制度背景的差異,盲目地響應(yīng)發(fā)達(dá)國家消費的示范,很可能是“邯鄲學(xué)步”,只學(xué)到些皮毛,反而把自己好的一面丟掉了。這一點在激進(jìn)的青少年身上體現(xiàn)得十分明顯。難怪林可先生說:“社會上盛行的‘韓流’現(xiàn)象,最具說服力。很多年輕人對這種潮流趨之若鶩,但也有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,這兩種現(xiàn)象都顯示了我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的不自信。”我們處在一個國際大交流的時代,隨著國外商業(yè)文化的涌入,應(yīng)該承認(rèn),商業(yè)文化在跨文化傳播中有其積極的特性。但由于傳統(tǒng)文化的弱勢地位,這種傳播越來越帶有一種話語霸權(quán)的味道,因此,它對傳統(tǒng)文化的破壞作用也越來越突出。結(jié)果,沒有這些東西的人們便不得不產(chǎn)生一種比人差一頭或不合時宜的感覺,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。 要樹立文化自信,必須依*一定的文化張力。文化張力主要是由精神文化作用于人而產(chǎn)生的觀念形態(tài)的張力,這種張力就是*弘揚主流文化、傳承先進(jìn)文化激發(fā)出來的。文化張力是來自歷史源頭之力,近乎民族精神力量的同義語。鑒于文化是永久制勝之本,當(dāng)今世界多元文化競爭愈演愈烈,各國都在采取種種措施強化民族文化張力,但更重要的還是取決于文化內(nèi)涵本身,一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,在強權(quán)政治面前也會立于不敗之地。 |